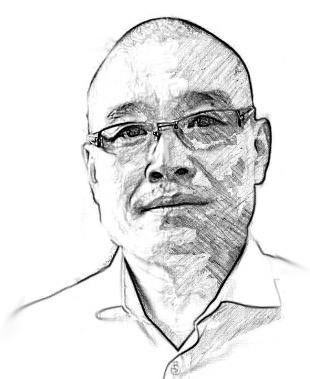旨在通過問卷,評估全球民眾對各國政府、媒體、企業及NGO信任度的2022年“全球信任晴雨表(Edelman Trust Barometer)”表明,政府和媒體加速了信任危機,相形于2020年下滑13個百分點。其中政府信任度52%,媒體50%,非政府組織59%,商業機構61%。領導力缺失令不信任成為默認選項,而高達76%民眾擔心“假消息”被視為武器。
作為倫理學基本概念,信任通常是指政治、經濟及社會三個層面的每個個體、團體,乃至國家之間在合作過程中對對方誠肯度和忠實度的期待和愿景,是彼此間意圖、能力、道德及精神風貌的整體表現。在彼此關聯過程中,如若因利益得失而降低道德權威,破壞行為規范乃至精神素養不受約束從而致使協調和美關系趨于緊張甚至喪失,即形成信任危機。
信任危機全球蔓延 中國社會健康安全
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傳統的“民主國家”明顯遭遇信任危機,多國政黨先后進入焦慮周期。溫和力量弱化和政治勢力極化令政治妥協作為民主政體擁有的基礎優勢加速崩潰。信任具有人性化亦富含超階級、跨意識特征,在特殊歷史階段和給定環境中動態進化。近年所流行的官民沖突和國家博弈即可幫助我們解釋為什么“不信任”像病毒一樣看似無影無蹤,但卻貽害無窮。
從日前美國俄亥俄毒氣泄露到希臘火車對撞,從臺灣蛋荒,肉荒和缺水少電再到法國強行突破憲法的退休改革,乃至6000家美國制造商一度聯合起訴政府賠款,聲討總統未能撤銷前政府對華關稅而失信,迫使民眾對政府不信任投票。凡此種種,皆是對管治階層的怨氣和詬病。最新調查顯示,美國民眾對兩黨信任較2021降低14%,選民低投票率折射了選民的政治冷漠和對政府的質疑。
信任危機正在全球吞噬以個體關系為基礎的傳統道德性社會信任體系。商業社會有異于農耕文明。網絡詐騙、經濟腐敗和政治丑聞在科技發展過程中亦步亦趨,繁衍滋生。社交媒體不實信息以訛傳訛,利益驅使下,野火般延燒不盡。促進公眾與專家對話,不失時機整治自媒體并實現專家與政經利益剝離以確保高效科學傳播中立價值,毋庸置疑。
交通的發展,互聯網的普及,專家之言的輿論導向,特別是媒體失信的鋪天蓋地,加深了社會猜忌,強化了信任危機,甚至令以社會良心和信任基石為基礎的真正意義上的學術權威日漸消弭。信任危機為不同文明的對話及各經濟體相互貿易中帶來的殺傷力均與過往不可同日而語。地區沖突惡化,民主政治滯后,政府信譽一瀉千里。
人類進步促使民眾對民生要求與日俱增。不讓期望變奢望,官民關系要重塑。民有所盼,政有所為,腳步測量民情,躬身諦聽訴求;各國近年來熱衷于不依不饒的國際紛爭,目光向外的“斗爭”,無意中忽視了內部矛盾和自身問題,“社會契約”必然難以恪守。從信任到信任危機或須臾之間但反向過程則風雨兼程。疑慮的種子一旦播下,信任瞬間就變異成任性。
在中國,近期流行“淄博現象”。看似不足掛齒的路邊燒烤,卻一夜之間激發全民熱情,對基層治理和機制創新提出了挑戰和思考,所謂指標性規則和量化的城管慣例以及民眾心目中形式和官僚陰影下文明城市的一系列制度在特殊時期為民生讓路,把民意筑牢。民眾從三年漫長的防疫抗疫夢魘中驚醒,對增加收入,尋求就業,釋放能量,成就自我的訴求格外突出。
國際環境的變化和世紀疫情的突襲已經不同程度對經濟秩序和社會治理造成嚴重沖擊,特殊背景下社會的非常規發展,要求各個地區根據不同情況及時調整策略從而實現因地制宜和與時俱進。”淄博現象“的順勢而為,深入民心,各級公職人員一線服務燒烤攤,飲食文化拋磚引玉走在前,引起全社會和各地區互學互助舉一反三,增加了民間和諧,官民互信,營造新氣氛,開拓新局面。
事實上,隨著國家經濟雙循環及高質量發展的深入實踐,全國各地已經呈現綠色經濟和聯動發展,為刺激消費和擴大內需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有機結合及增加大循環內生動力提供了條件。新型產業的興起和靈活機制的運轉,激活消費市場和文旅行業,基層政府創新思維,提升理念,避免百姓一邊深度焦慮,而另一方面管理階層直面困難難擔當,刻舟求劍念文件。
國際關系復雜多變 重塑信任任重道遠
信任是維持社會秩序的軟性機制和內生關系。世界根本性變革所造成的傳統斷裂以及制度性承諾的乏力是造成信任危機之核心。失常政治生活的積淀和爭奪市場的次生效應妨礙市場發育,造成經濟秩序紊亂,削弱管治威信和行政效能,影響國際關系的良性互動,引致國家及地區之間的信任關系在文化、經貿,乃至于不依不饒的斗爭中退化演變。
重構信任體系,需要完善制度運行機制。法制功能保障交易公平,但繼承傳統文化中具有普遍效力的元素才是重中之重。機構失信導致內耗,危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正向作用,而環境變化引起道德矛盾和道德困境,偏離價值取向和善惡觀念,助長實用主義和自我優先的局面。人無信不立,國無信則衰。信任危機是最大危機,而信仰崩潰是終極崩潰。
信任是社會發展和進步的基本元素而非人類的奢望和遙遠的記憶。肇始于西方的現代性囊括個人主義、理性主義、民主政治和進步觀念的價值要素。個體自由解放是現代性成就,但“遵守諾言要像守衛自己的榮譽一樣”。根植于不同歷史文化的價值觀對異質文明的嗤之以鼻只能導致誤讀。透過社會學理論,從背景、本體、文化、歷史和制度或可對信任及信任危機動因動因探究分析,抽絲剝繭。
人和人之間是這樣,國家之間和國際關系亦然。什葉派和遜尼派宗主國的伊朗和沙特兩個血雨腥風的世仇國家不久前在北京言和。化解夙怨雖任重道遠,但完全不同信仰國家的成功復交改善了中東格局,或將為全球地緣政治新時代帶來和平契機。伊沙恢復政治關系,詮釋了外交解決沖突的有效性。中方之于二者的公正魅力和信賴程度自然不言而喻。
國際關系錯綜復雜,各國利益糾葛難辨。雖然各種力量此消彼長,但和平曙光卻始終若隱若現。信任需要建立在互動和交流基礎之上,既不能退避三舍,更不可出爾反爾失守底線。俄烏戰爭處在危險邊緣和歷史轉折點,中國則被視為推動俄烏止戰,維護人類共同命運的核心與中堅。國際問題需要大家坐下來好好商談,全球視閾下的信任內涵可望在“中國方案”的實踐過程中得以縱深和延展。
“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遠。”尊重與理解是解鎖全球治理體系嚴重受創及單邊主義野蠻生長的癥結。破解信任赤字需要義利并蓄的倫理型國際關系,重利輕義強權政治則適得其反。“信任是國際關系粘合劑”,又是和諧,和平及合作加速器。東西文明差異和南北國家的失衡發展阻礙了全球公正與信任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卻異化了國際關系。國際政治不確定性正在強化國家實用主義,惟合作共贏才是共同發展的不二秘笈。
(原載于5月10日《聯合早報》,作者有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