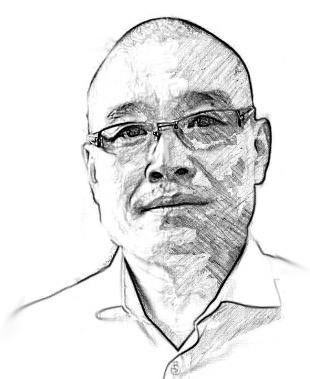近年來,教育改革呼聲益高,外語教育改革更是推波助瀾。學界甚至質疑未來英語專業設置的必要性,對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更是批判聲音不斷。筆者粗略梳理,縱橫比對,舊題新提,一孔之見,供外語教育工作者和專家學者交流探討。
目前,外語是中國基礎教育階段必修課之一。語言能夠開發少年兒童智力,增強交流表達技能,陶冶性情,拓展視野和開發思維,為大學教育和終身教育提供良好的理論基礎、實踐平臺和職業生涯興趣點,已經形成學術共識。
外語基礎教育旨在于培養學生綜合語言運用能力,加強在情感態度、學習策略、表現技能及文化知識諸維度的開發和訓練,以期實現學習動機、個人意志、合作參與、資源調動以及交往自信等品質的塑造。在日常詞匯、語言規則、信息傳遞及思想表達方面有所突破和創新,并在此過程中了解域外文化,抬升國際視野并增強國家意識和愛國情懷。
中小學校園長期以來一言堂填鴨式教育,機械模仿和未必人性的枯燥重復及被動記憶教育模式惡性循環,致使學生厭倦學習,懼怕外語,帶著慣性一路沖進大學校園,最終必將在繁多應用和實戰過程中因噎廢食,戲稱“一壺永遠燒不開的水”。中國外語教育要改革,教育工作者需要根據時代要求和社會特點進行戰略調整,以不斷適應新的發展要求和深層挑戰。除了拓展教學渠道等技術層面的調研之外,突出學生主體,尊重個體差異,采取靈活方式,積極體驗參與及開發教程資源亦屬舊題新提,移位審視。
根據兒童學習語言的特點和規律,教育心理學專家通常建議,首先保持幼兒語言的本能和好奇心。皮亞杰認為,“人為推動兒童超越其自然發展水平,無異于訓練動物在馬戲團表演雜技,這種做法對兒童成長并無益處”。兒童階段,孩子們喜歡語言而且表現出極好的語感和語言鑒賞力。”盡可能早的開發語言智力,從單詞句到雙詞句再到簡單句可以順勢而為“。語言環境的提供當然不可或缺。家庭、學校及社會三個維度形成基本框架結構,有意識有目的創造一個機制,比如,為嬰幼兒在視聽方面設計一套系統,下載一個軟件,甚至選定一個電視節目如”國家地理雜志”或者一個略有學習導向的游戲。在愉悅身心過程中,從自由到自覺,最后實現自律。
一個人的成長是本,而知識技能及道德就是末。根深必葉茂,本固必枝榮。學生發展是外語教育的出發點和終極歸宿。教育的全過程應該始終貫穿以人為本的核心要求,使學生的知情意行在課程的設計、執行和評價過程中充分彰顯;基礎教育又是一個個性教育的過程,實現學生個性發展和思維發散。個體差異不僅受到尊重,而且有的放矢,關注重點。當代社會呼喚個性,而個性又是創新之要件。學生的主體性和主觀能動性在語言學習過程中驅動力強勁,生發自然,取之不竭。積極構建學習評價系統,鼓勵學生自發自覺,促進學生人格發展,而教學材料的知識性、邏輯性和科學性在其本身趣味條件下,通過教師有意引導和評估體系動靜結合得到完整傳遞和深層滲透。
新的歷史時期,人才觀、人才標準和社會對人的要求與改革開放初期大相徑庭。越界、跨學科、復合型已經成為時下熱詞。傳統行業的消亡、新型職業的出現、人工智能的參與對人才規格提出空前挑戰。梁啟超曾經說過,“變法不變本源,而變枝葉,不變全體,而變一端,非徒無效,只增弊耳。” 1985年通過的“教育體制改革決定”鮮有落實。教學領域的改革亦并未列入國家教委工作日程逐一兌現。舊的教育理念、教學內容及方法依然占據教育主導地位“。”中國外語教育目標應該分層,讓學習者各取所需,各奔前程。“
改革開放30多年,各級各類學校外語專業學生通過不同考試平臺進入高一級或更多級現象突出。對于高層次人才來說,外語儼然成為人生職業上升階梯和越來越側重服務于諸學科研究。不過統計數據也表明,近年來通過國際機構考核以高分進入世界名校的所謂優秀學生“回爐”案例亦不鮮見。
全球理念和國際視野為外語教育提供了開發教育材料和學習內容的想象空間。與日俱進的社會發展和日新月異的生活方式也不折不扣提供了廣闊的研究背景和鮮活對象。新興科技衍生生鮮詞匯,視聽設備及互聯網信息也為外語教育搭建了動感平臺。“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教材教法陳舊、學術理論滯后、教學導向功利令學生疲于進取。把外語課視為不教授就學不會的知識課,也固化了傳統教育理念,局限了學生思維空間。早期靠強化背誦范文和寫作模版以應對各個層級考試之范式,如今捉襟見肘,尷尬難以避免,正如盧梭所說,“你開頭什么也不教,結果反而創造一個奇跡”。
筆者從事英語言文學及科技英語、外事外貿英語,法制警務英語諸領域教學三十余載,一路目睹和親歷中國英語教育的今生前世。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隨著對外開放和教育改革的深入,英語教育眾星托月,不可一世。”大學英語“作為公共外語被廣泛抬舉,大學英語教研機構在眾多高校特別是沿海地區及開放城市應運而生。外語系老師每學期兼任近十余個學系英語課還要舉辦各類講座和培訓班并不稀奇。其時過程中,英文老師不同程度由授業解惑演變為機械刻板模具商或者教書匠。
在深圳,各級政府向來都是學習型政府及外向型導向。特區成立之初,不同官階外訪、招商和出境公干均需要外語學習。即便移民抑或留學,第一關當屬強化外語。曾經有人戲言,每100個國人出境,至少不低于80人取道深圳,而其中至少2/3人士滯留深圳(深大)進修外語,當中不乏一線歌星、影星及社會名流。如今物是人非,往事隨風。人換了很多茬,書也更迭數個版本,但是,教育內容和教學方法依然換湯不換藥,原地踏步走。
“公共英語也應該到了顛覆傳統理念的時候”。CET作為標準化考試實施以來,成就了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大學生,40年來,從事外交,外事,外貿和外語教學人才數以萬計受惠于高校英語專業,但是,隨著“本土型”向“國際型”轉化和高等教育產業化國際化步伐趨快,應試和功利教育問題凸顯。內地高校有學者戲言,國內高校外語教育最大的變化乃學生學習更浮躁,知識更淺表。“作弊規模化、技術化和組織化不斷升級,而促進身心發展、提高學術水準和跨學科跨文化的外語教學不斷泛化,專業品質及專業品牌嚴重毀譽”。因此,隨著時代的變遷,國內千所公共英語及專業英語終究完成其使命,是否升級換代或者壽終正寢從而永久退出外語歷史舞臺,見仁見智,值得思考。
作為人文學科的英語專業事實上在多個高校并沒有依照人文學科要求架構大學生知識體系。涉及語言文學、國際交流、文化傳播、國際新聞及法律商務高端人才從英語專業脫穎而出的現實甚至難以和過往媲美,而課程系統的設計亦匱乏西方文明文化史、東西方哲學及經典社科類元素,造成畢業生在學術研究和應用實踐上后勁不足、乏善可陳。如若成就新型的既通曉外國語言文學又熟悉西語國家文史哲、既能跨界多學科交叉研究又能諳熟國際規則和全球事務,推動外語教育內涵式發展,著力英語工具性和人文性統籌兼顧,強化教師職業訓練和業務提升成為目前促進人才發展和社會進步之必然環節。
西南大學注重英語素質改革。語言技能課、文學欣賞課和文藝表演課使得外語教育多維度全方位融會貫通;上海外國語大學在語言文化教學中,“融合通史教育理念,以語言文化為內核,體現多元價值取向的外語課程群,凝練大學英語課程內涵,彰顯個性化創新特色”。
在香港,基礎英語教育教學目的明確,語言學習趣味性和交際性突出,英文的工具性和實用性凸顯,學生想象力和自我發展空間的培養直接導向創新性發展。教師通常把音樂、美術和手工融入英文教學活動之中,擴大教學外延的同時,深化了語言文化的內涵;在英文評估和測試方面,雖然聽說和筆試兼而有之,但通常試卷圖文并茂,以學生觀察力通過一定語境的解讀,技術地判斷學生語言水平和潛在能力。香港英文基礎教育中的教材銜接和教育手段相對完善。內地英文教師雖然含辛茹苦,鑒于社會環境和政策導向,在學術背景、學歷學力、能力態度、方法理念及教育精神諸方面始終亦難以企及。
香港小學英文課每周7-9節,但教師工作量卻28-30節課。因為多數英文教師均有跨學科背景和越界經歷。教師的交叉學科背景決定了教師的知識系統、思想結構和思維活躍度。不過,近年來,香港英文教育退化和淺表現象凸顯。基礎教育過程中過多的手工和社會實踐,一方面鍛煉了學生參與和合作能力,提高了動手和創新意識。但是,非語言的活動和過度的教具及互聯網依賴,弱化了學生語言思維的內在機能。在識字、書寫、閱讀和表達方面碎片化,和社會快速發展形成反差。在學術詞匯的掌握、科技信息的捕捉和書面內容深度理解諸方面,較歐美學生亦顯著滯后。
即便在香港高校,大學英文教育現狀也不容樂觀。教育課時消減,教學目標狹隘,學習動機過于功利。香港作為英文為官方語言的發達地區,為滿足社會之需要,大學英文改革也在持續之中。通常情況下,大一開設基礎英文課程,次年開始專門用途英文。港大第一和第二學年分別安排6個學分基礎英文課程,并為不同專業開始不同的ESP課程以實現語言的應用性;中文大學分別在第一、二、三學年分別安排4、3、2個學分的ESP課程。科大和理大亦因地制宜,各有側重。
英語作為傳統工具的學習和使用,在新的歷史時期已經賦予新的時代功能和意義。其內涵的縱深之需迫切要求其維度多元和外延拓寬。語言學習其實就是大海暢游,既要縱深潛入又要水面仰臥,可謂深入淺出,深呼吸之后也需要一吐為快。基礎階段的深耕細耘和高級階段的營養吮吸只有統籌兼顧,才能相得益彰。條條大路通羅馬。語言學習類也似行車。不管省道、縣道抑或鄉間小道,終究還是要轉軌換道切入高速才能快速抵達目標,以最短的時間和最高的效率同時領略高速兩側大自然美景,收獲至多新信息,新知識和新技術。
中國各層級學校在外語教材編寫、教育目的制定及教學方法設計諸方面,既需要側重語言基本功的穩扎穩打、人文素養提升和國際視野拓寬,又要顧及跨學科跨文化和學生思辨能力及批判精神的培養并適時進行信息化、通識化和科技化過度。英語教育不是專門人才的培養,而是“人文通史型、實踐性或者通用型人才”的鑄就。學界一度呼吁取消所謂外語(英語)專業,因為即便是所謂的專業英語包括所謂科技、商貿及其它專業外語,亦未必能夠在今天學術界抑或社會諸領域對號入座、一顯身手。世界格局的巨變,產業結構的調整乃至于世界觀方法論的革命均迫使學校及教育當局作出及時全面回應。
有專家指出,“課程實踐基礎上,高品質的通史內容通常在客觀上要求參與者動手動腦、查閱資料、分析研判,可謂由壓力變動力”。美國紐約大學(Global Perspective on Society)就是一個例證。要完成一個課程,大量的時間、精力甚至人力物力均有參與。“對于一套培訓方案而言,其課程 和容量是有上限的,通史內容的增添,勢必擠占所謂的專業的學時和內容”,所以,全球高校均會在大學基礎階段踐行通識教育。專業教育基礎之上的理想通識教育符合教育發展規律和自然發展路徑。
在國際環境紛攘背景之下,外語教育正在加速度陷入尷尬腹地。除了高校擴招和教育產業化一浪高過一浪,事實上,近年來也就沒有出臺太多的實質性舉措。通常情況下,一個所謂的“國標”或者“綱要“出臺之日就是落后于社會需要和時代創新之時。如若成就人才培養和外語教育歷史使命,有關教育政策的制定和落實已經急不可待。不過,這些問題在操作層面上會否涉及更多維度,那又是見仁見智、需要探討的其它話題。(原載:國際關系學院《翻譯教學與研究》。有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