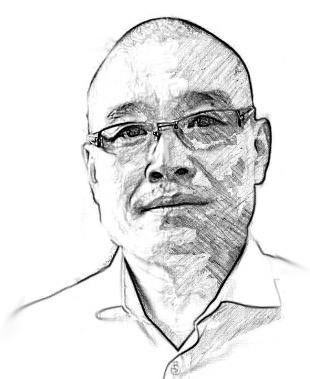今年五月中旬,在接受人民日報海外網經濟欄目專訪時,本人還曾津津樂道粵港澳大灣區前景與未來,并于稍前就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與發展存在的問題和港澳,日本及澳洲部分社會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在不同場合進行過探討與分析,也因此有過一些新的發現和思考。近期在深圳,香港等地多次召開的各層級公開和非公開關于香港,深圳和香港,香港和美國,中國和美國多個會議上,相關專家特別是中國內地高校和政府背景學者及政策決策人士幾乎無一例外,強調香港在國家發展和大灣區建設中無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對于如何解決曠日持久,每況愈下的香港現實問題開始少人問津,鮮有關注。要么泛泛而談,避重就輕;要么人云亦云,總之難有新意。
國內學術界“形式主義”和境外“實用主義”形成鮮明比對。一個新的課題似乎在香港亂局和國際不確定因素增多的大環境下,從學界,甚至精英階層開始萌生并迅速引起社會及媒體關注。這就是澳門特區產業結構,人口紅利,國際參與及與內地合作。著重著重探索澳門在其新的歷史時期所承載的歷史擔當、民族責任及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發展過程中的角色調整和重新定位。
事實上,粵港澳大灣區從最初學術研討到中央決策然后上升到國家戰略,從《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綱要》到《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先行示范區》,始終是一個從內涵到外延不斷豐富和完善的動態過程。九個內地城市及香港、澳門的角色扮演和功能定位也因此與時俱進,通過不斷互動和調整,形成互通有無,和諧適應之格局,從而取代傳統意義上的畫地為牢,各自為政,互相阻隔和你爭我搶。
《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提出要建設“一中心平臺”; 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支持澳門建設世界旅游休閑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平臺,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將澳門作為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與世界多種文明共存的交流基地,于是,澳門產業多元化框架雛形指曰可待。灣區人也同時預期粵港澳大灣區領導小組不失時機,集思廣義,根據新形勢新變化,高瞻遠矚補充出臺新形勢下的針對澳門在促進灣區社會經濟發展新政或意見。
澳門自身地理位置優越,發展優勢顯著,人杰地靈,政通人和,獲得了中央政府信任和支持。作為東西文化交匯點,其橋梁作用不言而喻。和香港一樣,澳門可以作為聯絡平臺,無縫對接國際市場,與歐盟,東盟,特別是葡語系國家開展投資、合作、并購及人民幣清算。利用在文教、科技、旅游及金融業得天獨厚之優勢,為國內市場的國際空間拓展提供大陸架及國外資本和項目進入中國內地提供渡口和橋梁。
近年來,澳門博彩業突飛猛進,早在二零零七年“路透社”就曾報稱澳門已經取代拉斯維加斯,成為世界新的“賭都”。但是,博彩業一家獨大,占據當地整體經濟產出的一半和澳門財政收入的近八成,這就無形中挷架和制約了其它行業的拓展和開發。產業結構的單一化導致市場功能失衡和偏廢,經濟體量終究難有突破。澳門地域狹小,人口不足香港的一成,造成競爭力不足,獨立性不強,對內輻射對外聯合力不從心,捉襟見肘。對于中國國家戰略的配合處于尷尬境地,始終為港人和國際社會所俯視。
然而,澳門大學楊鳴宇博士則認為,由于澳門人對中國認同度高,而且在十年前己通過國安法,抗爭力量難以凝聚。所以,穩定祥和的政治環境和市場繁榮的人文氣氛則為澳門的經濟騰飛提供了先決條件。相形而言,在香港,當基本法二十三條相關國家安全法立法時,則遭遇全面抵抗而擱置至今。這就是為什么日前北京四中全會強調香港迫切需要提高管治能力健全香港維護國安法律機制盡快落實二十三條立法之原委。
“十年河東 ,十年河西”。澳門的巨大潛力,連續多年釋放充分,發展前景不可限量。從中山粵澳合作示范區到橫琴中醫藥科技產園區,粵澳多個平臺已設置完備。澳門珠海合作開發萬山列島及“飛地經濟”也為澳門產業結構優化和內外功能化發展提供了地區級平臺。
十月二十六日,全國人大授權澳門特區對橫琴口岸澳方及有關延伸區實施管轄,這一“包括六大板塊授權,三個階段實施”的舉措“堪稱是法制保障重大改革的鮮活實踐”。“下一步,橫琴新區將報請國務院劃定澳門管轄區域面積,地理坐標和啟用日期”,橫琴管委會發改局王彥如是說。其實,隨著港珠澳大橋開通,澳門口岸管理區建成,作為國家發展戰略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已經邁上新臺階。
二零一七年五月十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澳門如何對接大灣區建設“文章強調,澳門的優勢:精準聯絡人。”科技創新是灣區經濟的動力引擎,澳門雖然實力較弱,其實,充分利用好周圍環境和橫琴,便會“風起南海,潮涌珠江”,有望在大灣區發展中成為舉世注目之科創黑馬“。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要研究在澳門建立以人民幣計價結算的證券市場“。近年來,澳門發展的特色金融涉及相當債券分銷和發行,而債券也是證券市場的組成部分。”當局亦正在委托國際顧問公司進行調研,著重強調方案務必符合國家之需,澳門之長“,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如是回應澳亞衛視。
今年六月,在考察盧森堡期間,梁司長也曾強調,澳門正發展特色金融,根據“一國兩制”,“一帶一路”倡議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政策優勢,為國家發展和澳門多元化,將結合澳門自身環境和國家賦予的平臺角色,以發展債券市場和完善金融基建為切入點,為外來投資者創造落戶及營商環境,循外向型金融服務業方向,為中國和葡語國家提供金融服務,為大灣區城市與葡語國家營造金融服務的撟梁。
隨著中央支持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投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明確澳門海域管理范圍、以及應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及地區問題,澳門特區始終一貫,不折不扣,為“一國兩制”的實踐,成功垂范,堪稱楷模。剛剛當選第五屆行政長官的賀一誠,上臺伊始便宣布加大大灣區城市合作,全力以赴推進“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加大人才培訓,關心青年工作,穩定和諧大局”,而上任特首崔世安也曾在澳門勞務網上指出:澳門民眾普遍認識到,澳門是國家主權下的I高度自治的特區。只有國家利益充分維護,特區利益才能保障。據此,澳門儼然成了”一國兩制“的成功案例。
”澳門長期以來很少有首先發聲的先例。但事實上,香港反送中運動對澳門影響頗大,特別在精神和思想層面,”澳門一位知名電影制作人說。然而,連續五個多月愈演愈烈的香港暴力活動并沒有沖擊到一江之隔的澳門。出奇的平靜環境為澳門市民帶來思考和啟示的機遇:臺灣國民黨,民進黨等黨派正你爭我搶,頻頻論戰,爭奪執政權;香港街頭依然硝煙彌漫,前途未卜,妖魔鬼怪四處橫行;而此時的澳門應該不失時機,抓住時機,順勢而為,捷足先登,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發展擔當更多歷史責任。
澳門回歸中國以來,已經創造了諸多經濟發展神話。一方面受益于“一國兩制”政策,另一方面則是國內改革開放大發展大繁榮帶來的機遇。如今,澳門再次處于歷史關鍵階段。“香港經濟十年最慘,唯盼中美貿易沖喜”。無休止的香港亂局,讓世人大跌眼鏡。但同時也為澳門帶來機遇和挑戰。正如香港大學盧兆興教授所言,“香港的失利意味著澳門的收益”。如何自覺自醒,找準位置,從而做大做強澳門,不失為對澳門人重大考驗和嚴峻挑戰。
香港的深度淪陷客觀上勢必成全和造就澳門。不久前,多家機構包括國際知名智庫和主流媒體相継岀籠統計學信息,披露香港動亂如何做大做強了新加坡。比如,高盛報告指出,”今年六到八月,有近四十億美元的投資從香港轉移到其亞州的競爭對手新加坡“。人才的流失,資本的出逃,自然令新加坡漁翁得利,如虎添翼,這是不爭的事實。深圳在今年八月十八日成為“示范”市之后的近三個月以來,卻遲遲未發現針對性措施和地方政策出臺,從而體現“深圳速度”,不失時機有效攔截外流人才和資金,盡管國家層面稍前已經出臺相關人口和人才政策。據人民日報十月三十一日報道,二十萬香港居民已申請內地居住證,但相對高階流入歐美和新加坡等國家尚無公開數據。內地城市包括深圳在內的國際性、國際化及與特殊的香港文化兼容程度雖然見仁見智,但國家政策支持和輿論引導不可或缺。
長期以來,有不少觀察家和學界先后提出上海及深圳取代香港金融中心的可能性再到香港可能功能性被澳門取代。紛紛擾擾,莫衷一是,因為香港在體制,法制的西化,具有上海和深圳無法替代的地方。“特定政治現象的出現通常是多種結構性因素長期交互作用下的結果,所以澳門也未必完全取代香港。“
眾所皆知,港澳的重大差異之一乃前者導向政治,后者則側重利益,澳門在可預見的未來不太可能香港化。港澳在政治制度上頗多相似,但澳門政府管控能力較香港強而澳門社會動員能力卻較香港低。這就是為什么有專家早期香港問題尚未大白于天下之前,曾經嘗試提出大灣區統一行政的構想,以期實現你中有我,血脈相連的有機體之緣故。雖然目前乍聽起來不可思議,沒有任何技術性可操作,但是規劃粵港澳大灣區之初衷足見一斑。
如今,香港問題??斷國際化、縱深化和復雜化。面對各種社會撕裂,家庭矛盾,許多港人惡夢纏繞,宿夜難寢。醫生拒收或者漠視受傷警員,學校成立特技表演和練兵場。醫院和校園自然成為暴力之源。目前,香港除了向國際社會輸出“暴力楷模”,“游擊戰術”,香港國際形象一敗涂地。甚至有學者大膽預言,林鄭四招未能解決香港風雨飄搖,反而岀現更多更復雜諸如三K黨之類組織。香港成為沖擊世界經濟“黑天鵝”可能性似乎若隱若現,時日可待。
國際社會廣泛認同香港事件己經嚴重阻礙大灣區建設進程。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未必能恢復元氣,愈合創傷。外交部駐港特派員指出,香港街頭暴力超越國界,病毒堪比非典,比沙士更致命。雖然香港是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占全球人民幣支付交易約百分之七十九,是力壓東京和新加坡僅次于倫敦和紐約的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雖然目前其股票未大跌根基尚未觸動,但是,若長此以往,對香港金融業打擊是毀滅性的,而且也勢必引起全球經濟逆轉。
上周末是西方國家的“鬼”節,香港街頭依舊“鬼哭狼嚎”。“黑魔謀癱港九,大舉毀店襲警“。”蒙面法”推出數日,仍然不見好轉。此消彼長,水漲船高。這個歷史上最愛神出鬼沒的彈丸之地,似乎再也很難與文明,文化與和諧宜居相提并論。港人面對各路“小鬼”,無人知曉何時“鐘馗”再現拿魔捉妖。
社會要發展,人類要進步,灣區要建設。現在大家都很清楚: 既然上海、深圳乃至澳門也許短期內無法取代香港,“再造香港”,那么,在大灣區及大中華區多成就一個金融中心又何妨? 更何況在社會經濟發生動蕩和不測之時,畢竟“東方不亮西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