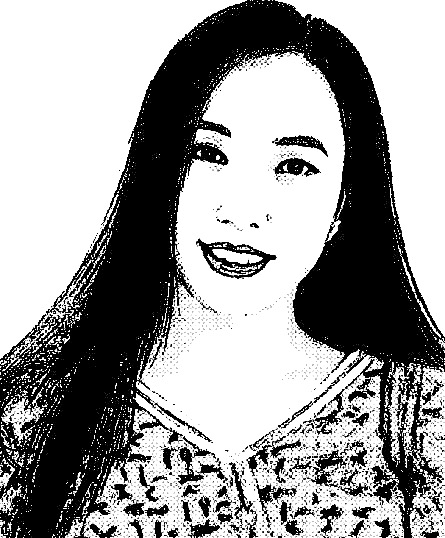第一次從一位世界500強企業的CEO口中聽到“from east to west”是在五年前。 彼時,Mitch Barn剛升任尼爾森全球首席執行官不久,在接受我的獨家采訪時他提到,從西學東漸到東學西漸,這是近年來全球化的重要轉向,而他本人的職業路徑也完美詮釋了這一趨勢。
從2008年到2011年,Mitch一直是尼爾森中國區的總裁。他強調這段“中國經驗”讓他受益匪淺,對他的職業生涯來說也至關重要。這三年的履歷不僅讓他更好的理解了中國在全球市場中的地位,也讓他具備了更全面的戰略視角,無論是從西方看東方亦或是從東方看西方。
2018年春節,我在微信上收到了Mitch從美國發來的節日祝福, 這多少讓我有點意外。而他后來的繼任者David Kenny在中國第一次見到我時,并沒有像其他的企業高管那樣和媒體交換名片,而是嫻熟的拿起手機和我互加微信。
David說他用微信已經有好一陣子了,而且他見中國客戶也一般是先加微信而不是交換名片。更讓我驚訝的是,這位現任尼爾森全球總裁早在十年前就已經使用過騰訊的即時交流工具QQ。雖然這和他當時的工作相關,但他對中國科技的了解程度著實讓我吃驚。
From West to East, then East to West。越來越多的外企高管都有了這方面的深刻體會:無論是在產品設計,人員培訓甚至是在技術研發方面,很多歐美在華企業早已逐步走上了東學西漸之路,甚至外企高管在中國的歷練也已成為其回國后進一步晉升的必備條件。這些林林總總的現象都折射出建國70年來中國社會的巨變,而這一輪“東學西漸”應該歸功于中國這些年不斷的創新和自我超越。
2013年10月,習近平主席在歐美同學會成立一百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中強調: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中華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稟賦。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惟創新者進,惟創新者強,惟創新者勝。
2015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指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創造歷史性機遇,催生智能制造、“互聯網+”、分享經濟等新科技、新經濟、新業態,蘊含巨大商機。
2016年"兩會"期間,“新經濟”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成為提升中國產業結構與增強經濟競爭力的題中之義。近年來,新經濟因素成果逐步顯現,正接過發展的“接力棒”,引領中國經濟駛向新航道。而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新經濟蓬勃發展的雙重驅動下,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持續穩步健康增長,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中國奇跡”。
“目前,我國已成為世界經濟第二大國、科研人員第一大國、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外匯儲備第一大國、對外投資第二大國。移動通信、現代核電、載人航天、量子科學、深海探測、超級計算等領域取得重大科技成果。”9月24日,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活動新聞中心第一場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發改委會副主任、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如是說。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一千多年前,外國使節、傳教士和商人沿著海陸兩條絲綢之路陸續把中國包括四大發明在內的科學技術傳往西方,之后又逐步深入到文化、哲學和中國社會制度的理性思考,為歐洲中世紀末期的社會變革提供了重要條件。而隨后明末清初和晚清民初兩個時期的“西學東漸”則加速了中國近代科技的發展。在這場循環往復的東西方文化技術交匯和融合過程中,占主動的都是國力強盛的一方。
欲知大道,必先為史。現如今的中國正逐步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更應發揚“有容乃大”的氣魄,不管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只要對我們有利,我們就吸收。海納百川才成就了中國文化之大,而在經濟領域,我們也一樣要秉承這樣的精神。
黨的十八大奠定了中國對外開放的新格局,而這個格局將會推動中國經濟在今后一段時間內逐步成為世界現代化的經濟大國和經濟強國。2018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2019 年中國將推動全方位對外開放: 中國對外開放的重點將從過去四十年的要素流量型的開放轉變為制度規則型的開放,在與主要西方國家的有效互動中,拓展對外開放的新局面。我們要用更大的開放來應對貿易摩擦,而不是固步自封。封閉曾是中國最大的痛點,而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也讓我們更清醒的認識到只有開放才能使我們進步。
而面對更為紛繁復雜的國內外環境,我們更要時刻警醒,居安思危。這不僅僅是物質層面的未雨綢繆,也關乎精神文化層面的共建。19世紀初,英國著名哲學家G. Lowes Dickinson在他的中國旅行隨筆《A Sacred Mountain》(指泰山)中提到“數百年前,他們在尚未高度富足的物質基礎上建立了偉大的文化上層建筑。西方人則在重建物質文明的同時毀壞了上層建筑 ...... 西方總是大談啟蒙中國,而我愿中國也能啟迪西方。”彼時,仍是西強我弱,Dickinson尚能發出這樣的感慨。如今,中國早已今非昔比,但我們仍需時時自省,牢記初心。
以史為鑒,以史為師,方能走的更為長遠。